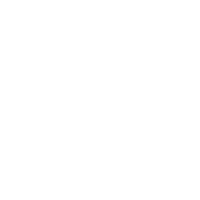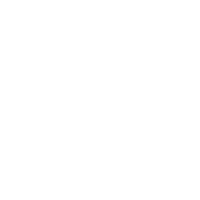近日,我院市政工程专业彭铭鑫、陈霖纯(指导老师柳君侠)在环境领域顶刊(Environmental Science & Technology)以“Smart Membrane with Reversible Superwetting Transition for On-Demand Antifouling and Self-Cleaning”为题发表最新研究成果。论文基于智能仿生理念,提出构建“超亲水/超疏水”智能转换来按需实现膜“抗污染/自清洁”,研究成果为膜法水处理中膜污染的高效控制提供新思路。

微滤和超滤广泛应用于水和废水处理领域,然而,膜污染是限制其广泛应用的技术瓶颈。通常来说,膜亲水改性能够提高膜抗污染能力。例如,受细胞膜抗粘附理念的启发(图1a),采用两性离子聚合物(ZPS)修饰膜表面(图1 b),ZPS能够吸引大量的水分子赋予膜超亲水特性。由于水合排斥能垒较强(图1e),ZPS膜能够有效防止污染物的靠近(图1b)。然而,一旦污染物附着在膜表面,超亲水材料(接触角WCAθ< 10°)对污染物的吸引势能较大(相较于超疏水材料,图1e),污染物不容易被清除。
与此相反,荷叶的自清洁能力源于其超疏水的低表面能蜡质层,水滴在这类表面呈球形并易于滚动,从而带走污泥及尘土(图1c)。虽然超疏水材料(θ> 150°)的自清洁能力较好,但水的渗透性较低,不能直接应用于水处理领域。与此同时,超疏水材料界面排斥能垒较弱(相比超亲水材料,图1e),在过滤阶段难以对污染物进行有效抵抗。因此,膜具有优异的抗污染能力并不意味着具有良好的清洗效果。已有的膜改性往往侧重于提升膜的抗污染能力,而对膜清洗效果的考虑相对欠缺。理想情况下,膜在过滤时应具有超亲水高排斥能,以实现其高抗污染;而在清洗时应具有超疏水低吸引能,如同荷叶自清洁机制,实现高效除污。面对过滤和清洗对膜浸润性(即亲疏水性)的相悖要求,如何实现技术的和谐统一成为膜材料设计与过程调控的关键挑战。

图1 膜表面浸润性对污染与清洗的影响。(a)仿生细胞膜;(b)超亲水膜高抗污染;(c)荷叶效应;(d)超疏水膜自清洁;(e)“污染物-膜”界面作用能。
材料表面的润湿行为受到其表面粗糙结构和化学成分的共同影响。增加表面粗糙度可以增强亲水性或疏水性,进而达到超亲水或超疏水状态。同时,通过施加外部刺激改变表面化学成分,有望改变其浸润性,促使亲/疏水转换。本文通过电化学沉积铜构建具有微纳米花瓣结构的铜网膜(图2c, d);由于铜氧化物的疏水性和粗糙结构对浸润性的强化作用,制备的铜网膜具有超疏水特性(154°,图3a)。这种超疏水行为可通过Cassie-Baxter润湿模型来解释,当水滴接触粗糙表面时,气囊会被困在表面的微小凹槽中,形成液-固界面和液-气界面。气囊的存在减少了水滴与粗糙结构的接触面积,从而强化了膜的疏水性(图3c左)。通过施加–20 V还原电压能够使膜表面疏水的铜氧化物(CuO & Cu2O,记为CunO)转换为亲水的单质铜(图2 e–h),且在持续电压20min内,膜表面水接触角从超疏水转变为超亲水状态(154°→0°,图3a)。根据Wenzel理论,在亲水性表面上,水滴可渗透到粗糙结构中,形成均匀的固-液界面。而粗糙结构增加了固-液接触面积,从而导致膜超亲水性(图3c右)。值得注意的是,在移除电压并将膜在100℃加热一小时,铜网膜水接触角变为153°,恢复超疏水特性(见图3b),这归因于加热过程中膜表面单质铜被氧化为疏水的CunO。通过交替施加电压和加热对所制备的铜网膜可逆转换进行评估,在十个循环中WCA在>150°和<10°之间切换,显示出其较高的耐用性(图3e)。这为过滤和清洗过程中按需实现膜抗污染和自清洁提供了理论前提。

图2.铜网基膜CMo(a, b)和电化学沉积膜CMe(c, d)的形貌图。电沉积膜在应用–20 V还原电压前(e, f)和后(g, h)的XPS图谱。

图 3.铜网膜表面可逆的超润湿转换。(a)施加–20 V电压和(b) 100℃加热情况下水滴在CMe表面上的接触角演变。(c)超浸润可逆转换过程示意图。(d)铜网膜的循环伏安(CV)曲线。(e) 可逆转换的10个循环的水接触角变化。
为了评估智能膜的抗污性能,本文选择了几种典型的原水:实际的珠江地表水、含藻水(直链硅藻为模拟物)和含有微塑料的水(聚乙烯醇为模拟物)。如图4a-c所示,在超疏水状态,粗糙结构减少了膜与水的接触面积,导致水流阻力增加,从而限制了水分子作用,膜的初始通量仅为12,500和17,500 LMH之间。然而,当转变为超亲水状态时,粗糙结构扩大了固相与液相之间的接触面积,从而促进了水分子的渗透性,水通量几乎翻倍,达到约30,000 LMH。电化学处理显著增强了膜在过滤过程中的抗污性能。无论使用何种进水,超亲水铜网的抗污性能都优于超疏水膜。在超亲水状态下,膜表面形成了连续的水膜,产生了强烈的水合排斥力,这一自发形成的壁垒最小化表面与污染物的接触,从而保护膜免受无机、有机和生物污染的影响(图4d左)。因此,即使在高初始通量下,也仅观察到较少的通量下降。相比之下,超疏水状态阻碍水分子靠近膜(图4d右),削弱了水合排斥力,并增加了对污染物的疏水吸引。因此,即使在相对较低的初始通量下,依然看到明显的通量衰减。因此,从超疏水转变为超亲水,不仅提高了产水量,还改善了操作稳定性。

图4.智能膜过滤(a)地表水、(b)含藻水和(c)微塑料水的通量变化情况;(d)超亲水和超疏水膜的抗污染行为。
膜具有优异的抗污性能并不代表具有良好的清洁效果。尽管超亲水铜网膜表现出较好的防污能力(图4 a–c),但其在相同污染情况下的清洗效率却低于超疏水膜(图5 a–c)。超亲水膜依赖强大的水合排斥力来抵抗污染物靠近,这与细胞膜防污相似。相比之下,超疏水膜通过其低表面能实现自清洁,这类似于荷叶效应,能够有效地去除膜上粘附的污垢。图5d和e进一步揭示了超浸润膜的自清洁行为。胶体铝粉均匀地涂覆在超亲水和超疏水铜网膜表面,通过注射器从样品的上端缓慢注入水,以观察液体在铜网表面上的清洗行为。如图5d1–d4所示,经过40秒的清洁,超亲水膜仅去除部分污染物,膜上残留着液体和固体的混合物。这是由于在超亲水状态下,水滴被卡在粗糙纹理中,阻碍了它们的移动,从而抑制了有效的清洗(图5d5)。相反,对于超疏水样品(图5e1–e4),水滴能够有效地带走了胶体污染物。这是因为在超疏水表面上,水滴悬浮在粗糙纹理之上,使得水滴能够轻松地在倾斜的表面上滚动(图5e5),进而有效地收集并去除表面杂质,实现了自清洁效果。

图5. (a) 地表水、(b)含藻水和(c)微塑料水污染膜的通量恢复效果;胶体铝污染的(d)超亲水膜和(f)超疏水膜的自清洁行为。

姓名:彭铭鑫:
学院: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
年级班级:2023级土木专硕2班
政治面貌:共青团员
个人突出事迹:
2024-2025年,获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一等奖、授权发明专利一项
2024-2025年,在环境及膜领域顶刊Environmental Science & Technology、Journal of Membrane Science、Desalination发表论文

姓名:陈霖纯
学院: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
年级班级:2022级土木专硕3班
政治面貌:共青团员
个人突出事迹:
2023-2024年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二等奖,在环境顶刊Water Research发表论文
2024-2025年 在环境及膜领域顶刊Environmental Science & Technology、Journal of Membrane Science发表论文
全文下载:  liu-et-al-2025-smart-membrane-with-reversible-superwetting-transition-for-on-demand-antifouling-and-self-cleaning.pdf
liu-et-al-2025-smart-membrane-with-reversible-superwetting-transition-for-on-demand-antifouling-and-self-cleaning.pdf